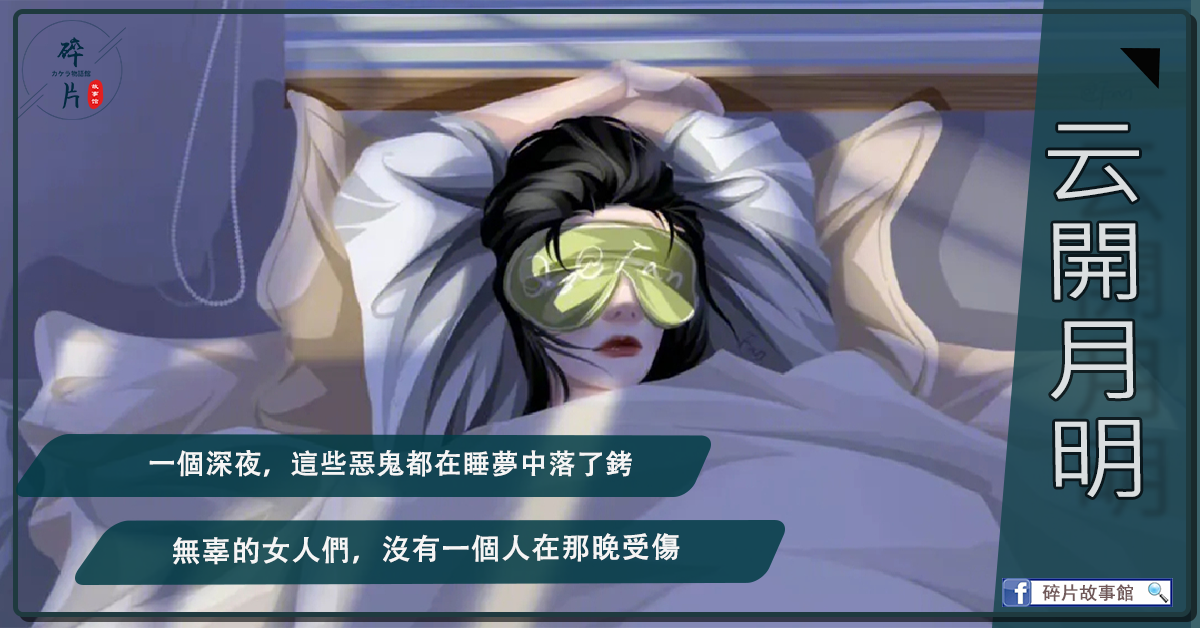《云開月明》第3章
我痛苦哀求,生怕他們報完警就走。
自稱是丈夫的男人還是不肯放開我,他和潑辣女人以我精神病發作為由,死死地控制住我。那個大學生想上前一步拽我,就被他們蠻橫地攔著,還用「不檢點」「想亂搞」為由羞辱他和我,大學生臉皮薄,只得退回去,緊捏著手機看向路口。
「姑娘別怕,阿姨也在這陪你,」剛剛叫住人販子的大媽也拿出了手機,「姑娘,我再給你報一遍警!老頭子,菜給你,你回去送貝貝上學,我今天非要看看,寧肯砸車都不跟他走,他到底是不是黑心肝的人販子!」
車主、大學生和大媽都報了警,就算是真的家人也不敢在警察來之前強行拉我上車,我雖然還是被人販子死死控制,身上、臉上都疼得要命,卻終于能稍稍安心。
「來姑娘,你聽聽。」大媽拿著手機靠近我,「瞪什麼眼睛,你倆非說這是自己家人不放手,我讓她聽聽電話總行吧?我一個老太太,不可能當著你們的面把她搶走吧?」
兩個控制我的人沒了話,瞪著眼看我低頭靠近聽筒。
大媽一手拿著手機,伸著另一只胳膊攏我,手機里電話忙音不止。
我忽然覺得不對,還沒等大喊出聲,身上就一陣刺痛。我張著嘴卻發不出聲,意識拼命掙扎,身體卻緩緩倒向自稱是丈夫的男人,靠在了他懷里。
「你這小姑娘不是耍我呢嗎!」大媽聲音洪亮得整條街都能聽見,「啊,我好心好意救你幫你報警,臨了臨了你說你倆是兩口子!」
男人裝著一副柔和穩重好丈夫的樣子,半拽半攬地把我帶到了車邊,大媽一步一步跟緊,牢牢地擋在我身前,阻隔了所有人看我的視線。
我動都動不了,只能任由他們用看上去是我自己走的樣子挪動我,心里又恨又悔,明明怨毒地瞪著大媽,眼皮卻一點一點下遮。
「還煩上我了?你讓我報警的時候怎麼不嫌我煩?」大媽說得更來勁了,「現在跟你男人黏黏糊糊地要上車,干缺德事騙我們的時候尋思什麼了!」
我被橫放在車座上,人販子團伙的人迅速上車歸位,油門和車門同時作響。
遠處零星幾個看熱鬧的罵出了聲,大概都是嫌我騙人同情耽誤時間,還有人連著前幾天「說人販子,吵架報警發現是兩口子」那件事一起罵在我頭上,沒有人看到,我動彈不得,眼里恨意滔天,卻只能看著車門一點點閉合。
熱浪一寸寸被隔絕,冷氣啃噬肺腑,最后一絲日光里,我只絕望地留下一滴淚。
應該很快,我就會像砸在地面那滴淚一樣,無聲無息地蒸干消失。
3.
醒來的時候,我已經不知什麼時候被人支了起來,頭靠在窗上,就像是旅途中睡著了一樣。
心里悔意翻騰,我不住后悔今天為什麼要去市場那里,又無比希望現在是個噩夢,只要醒來就什麼都沒有發生。千頭萬緒,我僅存的祈求藏在里面,一想就鉆心地疼。
雖然沒有監控,但那個大學生和被砸車的車主畢竟真的報了警。千萬千萬,要有人找到我。晚一點沒關系,只要能讓我活著!
我悄悄睜眼,注意到車里人員有些變化。
我身邊多了一個同樣被綁著的女人,應該是藥勁沒過,那女人爛肉一樣地攤著,頭頂在主駕駛椅背上,只露出半個煞白的下巴。
ADVERTISEMENT
「醒了?」
我心里咯噔一下,但也知道無法再裝下去。吃力地抬起頭,喉頭火燎一樣疼,我卻難以自抑地驚呼。
「看到我很驚訝?」男人從副駕駛探著頭,故意模仿我的驚叫。
是那個大學生!那個撥了報警電話的大學生!
他明明撥了報警電話,開的還是免提,我甚至驚懼之下都聽得清清楚楚……除非,一切都是假的,對面根本不是警察!
喉管刀割一樣疼,我遲緩地思考,好像終于想清楚了一切。
大學生和大媽是他們的人,大學生出現在那里的目的就是「報警」,開著免提,讓大家都知道他報了警。這種情況下,大概率沒人會重復報警,大家見有人管了,都能放下心來,該走的走,就算不走,也會先入為主地相信報警人是好人。
大媽應該就是專門對付我這種不聽話拼命想逃的女孩。危急時刻,最容易相信年長的同性,她一副打抱不平的樣子,騙了圍觀的人,讓他們在上班時間到了之后放心地離開;也騙了懼怕崩潰的我,然后作為最后一根稻草,借著由頭接近,扎針讓我失去意識。
原來剛剛拖著不肯走的不只是我,人販子也在等著上班時間到來!
我終于明白,卻已經遲了,只能寄希望于有人在現場看見了這輛車的車牌號,或者恰好拍到。
「季云是吧?我叫肖維,以后可以叫我維哥。你猜,」大學生笑得不懷好意,臉上紫色的胎記和面中那顆大痣跟著波動,「這輛車的車牌號是多少?」
我心里咯噔一跳,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「猜不出來?我給你看看——」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